真正理解布施
曾经有不少佛教人士为了宣传布施与财产无关,而与发心有关。比如这个故事沁入人心:
你有两个亲戚,一个穷,一个富。
穷亲戚一个月吃不上一顿肉;富亲戚是亿万富翁。你去富亲戚家拜访他,他给你一千块钱,“晚上我就不陪你吃饭了,你想吃什么自己买”;你去穷亲戚家,他杀了唯一的老母鸡招待你。
布施的功德当然不能从一顿饭的开销上判断。要从他们的心上判断。更准确地说,是心的功能和它引起的语言和动作。
这是硬核佛学的解释,用四句偈来概括,叫:“由此舍名施,谓为供为益,身语及能发,此招大富果。”
你看,布施在这里面等同于施舍,也就是舍去对于他最宝贵的东西还是随便的东西。
然而,真正在金刚经里面会告诉你,根本就没有什么布施。
‘菩萨于法,应无所住行于布施,所谓不住色布施,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。须菩提!菩萨应如是布施,不住于相。何以故?若菩萨不住相布施,其福德不可思量。
无相,所以无才是最大的
无论是想要追求成佛,还是追求自己成为最大的布施主,甚至刻到功德碑上。这就成为了“我执”的另一种态度。《了凡四训》是善书,这本书给了许多人一个做善事的方便法门。在这里面,做好事最好的就是布施。又分为法布施、财布施、无畏布施。然而,一说布施,肯定是从我的角度看出来。
星云大师说过:什么都是我的,什么都不是我的。本来无一物,何处惹尘埃。当然了,我觉得这里面如果加上“永远”,这就好理解的。
比如房子永远是你的吗?伴侣永远是你的吗?孩子永远是你的吗?理论永远是你的吗?……
人的肉身离开世界之后,如果没有谁记住你,你还会这么想吗?
换句话说,help,帮助这个词,实际上没有谁帮助谁,没有谁怜悯谁。我们这个世界上来来去去那么多人,说的话、做的事,能帮助他人,是因为他人的造化应该得到的。就算我不说,下一时刻他也会从别的地方获得。
佛,永远是无边无际的,是虚空的。正是因为空,所以无相无形。
数学中有一个符号,叫做∞,没错,就是无穷。
佛法因念而起,因念而灭
正因为有种种执着妄想,所以佛法才会存在。执着妄想越大,佛法就越硬核。相反,如果你做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想的,没有什么佛法。
正如同做事情,你如果偏要达到某个目标,往往达不到。正所谓是“有心栽花花不开,无心插柳柳成荫”。
所以,在金刚经中,实际上趋向于道教的哲学,那就是一切顺其自然,与自然合为一体便是好的。
道教的一位先生讲过一句话作为今天的结尾:
对于修行而言,来不是偶然,走不是必然。但行好事,莫问前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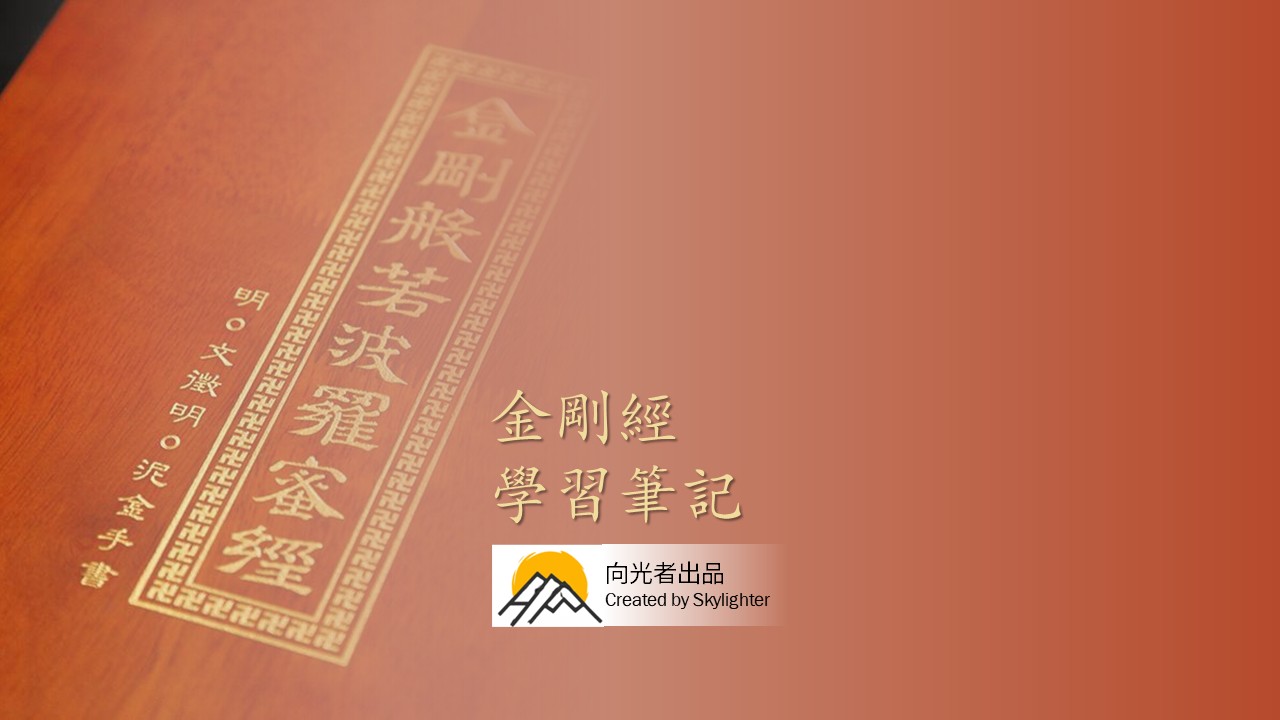
发表回复